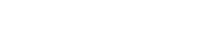到头来还是适合送给家人的康乃馨。
如愿以偿买到花的小钟心情畅快许多。以前的枝剪留给敬亭没有带来,她又买了一只同款,回到家优哉游哉地剪枝插花。四十五度角斜切,叶子剪去。本想一边构思本周的语文作文,却分外认真地思考起家人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近来,她时常感受到一股冲动,想要和他结婚,名正言顺留在他身边。命运无常,至少到目前,还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保证她们永远选择彼此,散了也就散了。好像只有被契约束缚着,平淡相守的日常能一直继续下去,像进入一段漫长的冬眠。
但这样的企盼也让她绝望。失去自由的她们不会幸福,爱情终将被束缚磨损得面目全非。她们的灵魂像月相变化般此消彼长,互相消化。沉寂的余生一眼望得到头。
自己真的准备好接受这样的命运吗?
摆好角度的花枝一不留神就偏了个方向歪倒下来。
她想了很多办法固定,才差强人意完成第一件插花。花枝没有全部用上,她又将剩下的插在椭球形杯子里。
另一边的作文毫无进展。眼看周末假期过半,她有些焦虑,在网上满地找素材,中途却罪恶地点进一条玉桂狗旋转的视频。就看一眼,她这样想着,身体却不受控制地看了将近一个小时,反应过来天已暗了。
这破作文弄得小钟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她越写不出反越较劲,一会趴在桌上,一会滚道地上,仿佛姿势的改变能玄学出灵感。但是没有,她绞尽脑汁写到无话可说,竟然连一页纸都没写满,前方满四百字的地标像永远到不了的彼岸。
握着笔却写不出东西,小钟干脆在第二页的空白处画花。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终于调理好了。而她惆怅地想,自己果真是没有一点读书的天赋。就算大钟一直安慰,说读书是一件有投入有回报的事,只要心无旁骛,普通人的资质就能拿到很好看的成绩,但她好像连普通人都够不上。高中和初中完全不一样了,她已经很努力去学,成绩却全无起色。
她像鸵鸟一样埋下头。想要逃避的心情很快让她睡着,口水流到作文纸上。神智清醒地见证这一切,也在香甜的梦里不亦乐乎,抱着小狗旋转,无尽旋转,旋转。
大钟面色苍白地回到家。她连忙跑回自己的位置装睡。
糟糕,忘记给他介绍花了。不过他看见花笑了笑,应是中意的意思吧。小钟暗喜,忘记自己手边全是摸鱼一整天的证明。他把会硌到她睡觉小玩意全都挪开。她怕再装下去就露馅,揉着睡眼醒来,迷迷糊糊道:“你回来了。”
他以为自己将她吵醒,不知所措地收回手。
小钟也有一刹愣神,娇嗔怪道:“你已经冷落我一整天了。”
“也是。”他伸出手想将她接住。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让向对方,反而严严实实跌上沙发,脑袋也撞在一起。他暗忍着笑意问,“我该怎么做?像成人电影演出的那样,一进来就强吻,把你按在墙上,扒掉裤子?”
“太夸张了。我不喜欢那样。”
“我也不喜欢。”他道,“今天很累了。你能上来自己动吗?”
和她预想的一样,这才是他的趣味。每次嘴上这么说着,一副他很柔弱任人摆布的模样,真到卖力的时候又干得比谁都狠。
她捧着烧红的脸,迫不及待沉入一场新的春梦,稀里糊涂说一堆自己也不懂的话,翻身下地,光脚踩出哒哒哒的声音。阴雨天气的空气有些闷,高层房屋的墙壁不容易浸满水珠,无形的湿意仍像精灵一样漂浮在半空。
外面又下雨了吗?她问,但看他干净的裤管,心中已暗有答案。
梦想中的他该更狼狈一点,该在理智崩溃的边缘勉强维持一线尊严。
她攀住他修长的指节,双手合成缠绕的锁扣。他的手还残留着室外的冷意,脉搏微弱的热意宛若生长的小芽。她把头深深地埋下去,衔起深红色的果冻顶,舔咬得晶莹剔透。半遮半露的腰线隐微起伏,破开一角的衣摆像小狗啃过。
雨声和着奶油泡沫的甜味渐泛上来。
他的眼中似藏着星星,跟随睫毛的颤动一闪一闪,似是很想要求饶,却碍于大人的身份不敢轻易言语。她暗暗使坏咬向深处,他才挣出一手,挠着她的下巴,毫无威严地命令道:不许再弄了。
熊孩子不把搞不定自己的大人放在眼里。
手臂忽然被飞来的蚊虫蛰了下,一阵酥麻,他把她抱上膝弯。
梦以外的她也转换成同样的姿势俯趴着。
“手,手……”
他把她挤在角落的手揪出来平放。她还红着脸痴笑,摇摇晃晃撞进更深的梦。
雨流在玻璃窗的外层交织又分离,失真的倒影似一片迷雾,将整座房间围困作孤城。忙碌害得她很久没时间剪发,现在头发已有及腰那么长。他捧着她回卧室,似捧着一件毛绒玩具。
这次他小心翼翼检查好避孕贴,谨慎太过,几乎让人没劲。做爱里愉悦和安全常是不能共存的选项,她在这之间冒冒失失地顾此失彼,像孩童贪吃那样沉溺于放荡。
缠绵的注视底下,再寻常的一举一动都带有挑逗的味道。她坐在他腰间,迟疑许久才缓缓脱去毛衣,换以双手夹捧乳房。白玉的软肉却不懂得纤细的娇怯,放不住也拦不住。垂坠的乌发垂在外面,犹未展开束缚时的折皱,末端像藤蔓一样绕在他的指上。
他若即若离勾引她倾身,湿润的性器官像充气的海绵泡挤向一处,撑开柔脆的水声。隔靴搔痒的快意最难捱。阴户情不自禁含向近在咫尺的玉柱,脊背酥麻得无力,她就快连腰也抬不起来。他明知自己主动一下就能让彼此解脱,却饶有兴味地看她绕一大圈弯路。她嘴上说着狠话,却拿他没有办法。
动一动,她咬唇央求。
他不回应,偏坏心地拍她屁股。
一把年纪还跟小孩一样。
她忘记自己有没有把内心的想法如实说出,只知睁开眼时,事情全都变了。
梦只是一场梦,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正抱着睡觉的她看书。
现实中的她们对话完全不同。
“心情不好?”小钟问。
如果他很好,不会这样徒增麻烦地抱着她。
大钟点头。
小钟抬起手,试图在他的半边脸上扯出笑意,“被说了什么,这么不开心?”
他的语声低弱,“问我什么时候换工作,还有催婚、催生,大人标准的三件套。”
“换工作?人民教师,他们还不满意?体面、稳定、离家近,放在别人家已经是大孝子了。”
“我有个发小,同个大学同年毕业,明年都能升正处了。”
小钟瑟瑟发抖。即便她这两年受敬亭的熏陶,也算知道三十岁干到正处并不容易,能听懂他的意思,但还是深深感到自己掺和不进他关于人生选择的话题。
她摸不准他的想法,自然不知怎样安慰,尬聊道:“果然人不能跟人比。”
“我知道的。”他淡然道,看样子只是被缠人的唠叨烦到。
小钟反观迷茫的自己,不禁有些感慨,“真好,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很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不在,我都不知自己要干什么。”
想要和他结婚的念头又一度占据脑海。
“做什么都好。只有先去做了,才更清楚哪些是自己想要的。”
大钟多少察觉到她对他的过分依恋,却没有认真纠正这种畸形的观念。反正她想将他当成世界的中心,对他不算是坏处。
小钟顿感恶寒。原来亲人之间的互相吞噬,最初就萌生微不足道的私念?就算朝夕相对,亲密无间,她们也没法真正分担各自的痛苦。
他的人生比起她来,几乎称得上一帆风顺,就算处在低谷也被恰到好处的地步,没有真正尝过山穷水尽的滋味。他对世事看得很淡,有他淡的底气,但是小钟没有。就算好言好语地劝着,他不懂得她心里难以和解的痛苦,还以为是她太过焦虑,年纪还小。
隔膜的感觉像被孤身丢进深渊。她不明白为何自己的初恋会谈成现在这种模样。明明本该是青春美好的事,她却一天到晚担心这那,怕被人发现,怕意外怀孕,怕被他丢弃以后无处可去,怕人生彻底烂掉。
“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大钟揉着她的脑壳,“周末多做些喜欢的事吧,不想做的事情不用勉强。我看到你的插花了,很有花鸟画的韵味。第一眼就被治愈了。”
他说她勉强,应该看到了糟糕的作文,实在觉得惨不忍睹吧。太羞耻了,简直像光着屁股被揪住一样。
小钟急匆匆地给自己找台阶下,“我本来就不适合读书。”
然而,她合该接受这份无条件的溺爱,似金丝雀被豢养吗?
果然还是不甘心吧。
大钟弯腰抱她,但她将他推开,焦躁不安地跳起来。
“我不能一直这样摆烂下去。”
“为什么不继续做擅长的事?正好之前的画在网上很受欢迎,往这个方向努力看看呢?”大钟叫住她,冷静地分析利害。
“但这不代表我能画出能卖的作品。毕竟我是半路出家,还是学国画的,比不过那些画了十几二十年的科班大佬。网友肯定我,好像只是善意地鼓励一个爱画画的小姑娘,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你不也自己画了十多年吗?你的十年不是十年?”
“那不一样。”小钟急道。
大钟又退一步,“只是当成爱好,也不再画?”
“现在哪有这个心情。”她黯然垂头,“我觉得自己没有出路了。果然还是好好读书来得正经吧。”
“是什么人、什么事让你不敢再提笔了?”大钟相当锐利地明知故问。
憋屈已久的小钟当场炸毛,“你少自以为是。我不想画就是不想画,没有别的理由。”
其实很想画,只是找借口逃避的心情占了上风。吼出相反的话时小钟才意识到。
他耐着性子讨好媚笑,埋首吻她的指尖,黯淡的眼神却藏不住倦意,“为我再画一次吧。”
还是一样的话。既然劝过没用,又何必一说再说?如果作画的意义是为别人,那她更不想提笔了。往昔被辜负或背叛的种种还历历在目。约定了陪伴的人最后都离她而去,她还一个人傻乎乎等在原地。
小钟非但没领情,反而觉得他很烦,“别把我当傻子哄。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我不会为任何人画,别再说了。”
大钟也不客气,转身将她圈进角落,逼她直视自己的眼睛,“照你这么说,因为别人放弃自己想做的事,不是一样愚蠢?”
她蓄了一股劲大声道:“我没有——”
他提前察觉到小钟要吵架,用吻封了唇,不让她再说一句。
气恼变成崩溃,她拼命反抗,扯住他的手臂,两个人纠缠着滚落到地上。她忍着痛从他身上爬起,抬头看见耀眼的灯光,忽然感到自己反抗他也毫无意义,哇的一声大哭出来。
他会任由她欺负,但现实不会。
“不说这个了。”
大钟的不战而退并非谦让,更像是轻蔑于她,这反倒激发小钟恋战的心思。她当即抬手甩了他一巴掌。
这一下打得很重,自己的手也失去知觉麻痛许久,她不敢想象大钟的感受。
他的脑袋侧敲到地板,头发凌乱得飞散,发丝的反光处不细看就像白发,似比平日更柔软。
小钟非但没有怜惜,反而从中感受到无法无天、暴戾的快意。掌控的感觉像吸毒一样让人上瘾。
终于,终于她可以将身上背负的一切通通发泄出去。
“所以呢?”大钟仍望着别处,冷冷问,“我要怎么做你才满意?”
另一只手垂在他的心窝,剧烈的跳动炽热,恍若再进一寸,就能将他的心脏握进手中。她用力抓下去,他仍是不为所动的姿态。
大钟就是这点最让她讨厌。高高在上,不把人放在眼里,对什么事都淡淡的,漠不关心。无论怎样激他都像拳头打在棉花上,一会将她当成无知小孩哄骗,一会又希望她足够成熟,能冷静独立地决定很多大事。哪怕在相识的过程中,他给了她很多意外的心动,讨厌也一直没有改变。
没法和解的。
小钟龇牙咧嘴。
“如果是住在一起让你不自在,那就分开住。我给你在学校附近找房子,钱的事不用担心。我会时常来看你。”大钟道。
这一天比想象中更快来了。既然想好体面周全的方式,也就是真心想赶她走。小钟也恨阴晴不定的自己,可情绪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怎么都拴不住。
他的话很明白,分开未尝不是一种对彼此都好的选择。但她的自尊心难以接受。被她一手搞砸的事情已经太多。如果连和他同居都做不到,她好像就真的一无是处了。
“不要……不要赶我走。我会……我会控制自己的脾气。”
小钟慌慌张张将他松开,佝偻着腰啜泣,渐渐萎在地上。
哭了一会,他便从后将她圈住,娴熟地擦眼泪,似她自己身上多长了两只手,并沙哑着劝道:“我只是看你这些天太累了。算了,也放心不下你一个人。”
小钟为自己还被爱着感到庆幸又罪恶。毫无疑问,这是她恶劣的地方,好像每次都要闹到事情弄坏,才能够检验他的真心,像“狼来了”的游戏。
还能奏效几次呢?
不管了。至少现在,她可以释怀那些不着边际的远虑,痛痛快快哭一场。
“你也太能忍了,憋这么久才哭出来。”他拍着她的肩道。
止住哭泣许久,堵塞的鼻子才重新闻到他身上的幽香。雨过天晴的感觉很安宁。她望着天花板自嘲道,“我怎么总在你面前哭?”
“说明你还年轻,我是哭不动了。”
她听他的语声有些怪,反手搓他的脸,指尖却碰到似有若无的潮意。
“你哭了。”
他的呼吸声沉重,久无回应。
小钟没想到自己对他的影响竟会这么大,或许她坏掉的时候他也坏掉了。
“白痴。”她温柔又怜惜地骂,带着一点不想说话的嫌弃。
他侧头来咬她的唇,一回回都被躲开。她故意往他嘴边塞橘子嘲弄,却一不留神被捉住手腕,掀翻在地。
“干嘛?”大钟红着脸,眼眶湿润,又变成流泪猫猫的样子,想凶也凶不起来。
这模样教她怎么看怎么怪。
是不是有几分像自己?他以前应该不是这样。
小钟皱起眉又要恼。
他连忙拉回她的注意力,“是不是非要我说,乖乖做我的女人,你才开心?”
如愿以偿买到花的小钟心情畅快许多。以前的枝剪留给敬亭没有带来,她又买了一只同款,回到家优哉游哉地剪枝插花。四十五度角斜切,叶子剪去。本想一边构思本周的语文作文,却分外认真地思考起家人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近来,她时常感受到一股冲动,想要和他结婚,名正言顺留在他身边。命运无常,至少到目前,还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保证她们永远选择彼此,散了也就散了。好像只有被契约束缚着,平淡相守的日常能一直继续下去,像进入一段漫长的冬眠。
但这样的企盼也让她绝望。失去自由的她们不会幸福,爱情终将被束缚磨损得面目全非。她们的灵魂像月相变化般此消彼长,互相消化。沉寂的余生一眼望得到头。
自己真的准备好接受这样的命运吗?
摆好角度的花枝一不留神就偏了个方向歪倒下来。
她想了很多办法固定,才差强人意完成第一件插花。花枝没有全部用上,她又将剩下的插在椭球形杯子里。
另一边的作文毫无进展。眼看周末假期过半,她有些焦虑,在网上满地找素材,中途却罪恶地点进一条玉桂狗旋转的视频。就看一眼,她这样想着,身体却不受控制地看了将近一个小时,反应过来天已暗了。
这破作文弄得小钟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她越写不出反越较劲,一会趴在桌上,一会滚道地上,仿佛姿势的改变能玄学出灵感。但是没有,她绞尽脑汁写到无话可说,竟然连一页纸都没写满,前方满四百字的地标像永远到不了的彼岸。
握着笔却写不出东西,小钟干脆在第二页的空白处画花。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终于调理好了。而她惆怅地想,自己果真是没有一点读书的天赋。就算大钟一直安慰,说读书是一件有投入有回报的事,只要心无旁骛,普通人的资质就能拿到很好看的成绩,但她好像连普通人都够不上。高中和初中完全不一样了,她已经很努力去学,成绩却全无起色。
她像鸵鸟一样埋下头。想要逃避的心情很快让她睡着,口水流到作文纸上。神智清醒地见证这一切,也在香甜的梦里不亦乐乎,抱着小狗旋转,无尽旋转,旋转。
大钟面色苍白地回到家。她连忙跑回自己的位置装睡。
糟糕,忘记给他介绍花了。不过他看见花笑了笑,应是中意的意思吧。小钟暗喜,忘记自己手边全是摸鱼一整天的证明。他把会硌到她睡觉小玩意全都挪开。她怕再装下去就露馅,揉着睡眼醒来,迷迷糊糊道:“你回来了。”
他以为自己将她吵醒,不知所措地收回手。
小钟也有一刹愣神,娇嗔怪道:“你已经冷落我一整天了。”
“也是。”他伸出手想将她接住。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让向对方,反而严严实实跌上沙发,脑袋也撞在一起。他暗忍着笑意问,“我该怎么做?像成人电影演出的那样,一进来就强吻,把你按在墙上,扒掉裤子?”
“太夸张了。我不喜欢那样。”
“我也不喜欢。”他道,“今天很累了。你能上来自己动吗?”
和她预想的一样,这才是他的趣味。每次嘴上这么说着,一副他很柔弱任人摆布的模样,真到卖力的时候又干得比谁都狠。
她捧着烧红的脸,迫不及待沉入一场新的春梦,稀里糊涂说一堆自己也不懂的话,翻身下地,光脚踩出哒哒哒的声音。阴雨天气的空气有些闷,高层房屋的墙壁不容易浸满水珠,无形的湿意仍像精灵一样漂浮在半空。
外面又下雨了吗?她问,但看他干净的裤管,心中已暗有答案。
梦想中的他该更狼狈一点,该在理智崩溃的边缘勉强维持一线尊严。
她攀住他修长的指节,双手合成缠绕的锁扣。他的手还残留着室外的冷意,脉搏微弱的热意宛若生长的小芽。她把头深深地埋下去,衔起深红色的果冻顶,舔咬得晶莹剔透。半遮半露的腰线隐微起伏,破开一角的衣摆像小狗啃过。
雨声和着奶油泡沫的甜味渐泛上来。
他的眼中似藏着星星,跟随睫毛的颤动一闪一闪,似是很想要求饶,却碍于大人的身份不敢轻易言语。她暗暗使坏咬向深处,他才挣出一手,挠着她的下巴,毫无威严地命令道:不许再弄了。
熊孩子不把搞不定自己的大人放在眼里。
手臂忽然被飞来的蚊虫蛰了下,一阵酥麻,他把她抱上膝弯。
梦以外的她也转换成同样的姿势俯趴着。
“手,手……”
他把她挤在角落的手揪出来平放。她还红着脸痴笑,摇摇晃晃撞进更深的梦。
雨流在玻璃窗的外层交织又分离,失真的倒影似一片迷雾,将整座房间围困作孤城。忙碌害得她很久没时间剪发,现在头发已有及腰那么长。他捧着她回卧室,似捧着一件毛绒玩具。
这次他小心翼翼检查好避孕贴,谨慎太过,几乎让人没劲。做爱里愉悦和安全常是不能共存的选项,她在这之间冒冒失失地顾此失彼,像孩童贪吃那样沉溺于放荡。
缠绵的注视底下,再寻常的一举一动都带有挑逗的味道。她坐在他腰间,迟疑许久才缓缓脱去毛衣,换以双手夹捧乳房。白玉的软肉却不懂得纤细的娇怯,放不住也拦不住。垂坠的乌发垂在外面,犹未展开束缚时的折皱,末端像藤蔓一样绕在他的指上。
他若即若离勾引她倾身,湿润的性器官像充气的海绵泡挤向一处,撑开柔脆的水声。隔靴搔痒的快意最难捱。阴户情不自禁含向近在咫尺的玉柱,脊背酥麻得无力,她就快连腰也抬不起来。他明知自己主动一下就能让彼此解脱,却饶有兴味地看她绕一大圈弯路。她嘴上说着狠话,却拿他没有办法。
动一动,她咬唇央求。
他不回应,偏坏心地拍她屁股。
一把年纪还跟小孩一样。
她忘记自己有没有把内心的想法如实说出,只知睁开眼时,事情全都变了。
梦只是一场梦,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正抱着睡觉的她看书。
现实中的她们对话完全不同。
“心情不好?”小钟问。
如果他很好,不会这样徒增麻烦地抱着她。
大钟点头。
小钟抬起手,试图在他的半边脸上扯出笑意,“被说了什么,这么不开心?”
他的语声低弱,“问我什么时候换工作,还有催婚、催生,大人标准的三件套。”
“换工作?人民教师,他们还不满意?体面、稳定、离家近,放在别人家已经是大孝子了。”
“我有个发小,同个大学同年毕业,明年都能升正处了。”
小钟瑟瑟发抖。即便她这两年受敬亭的熏陶,也算知道三十岁干到正处并不容易,能听懂他的意思,但还是深深感到自己掺和不进他关于人生选择的话题。
她摸不准他的想法,自然不知怎样安慰,尬聊道:“果然人不能跟人比。”
“我知道的。”他淡然道,看样子只是被缠人的唠叨烦到。
小钟反观迷茫的自己,不禁有些感慨,“真好,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很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不在,我都不知自己要干什么。”
想要和他结婚的念头又一度占据脑海。
“做什么都好。只有先去做了,才更清楚哪些是自己想要的。”
大钟多少察觉到她对他的过分依恋,却没有认真纠正这种畸形的观念。反正她想将他当成世界的中心,对他不算是坏处。
小钟顿感恶寒。原来亲人之间的互相吞噬,最初就萌生微不足道的私念?就算朝夕相对,亲密无间,她们也没法真正分担各自的痛苦。
他的人生比起她来,几乎称得上一帆风顺,就算处在低谷也被恰到好处的地步,没有真正尝过山穷水尽的滋味。他对世事看得很淡,有他淡的底气,但是小钟没有。就算好言好语地劝着,他不懂得她心里难以和解的痛苦,还以为是她太过焦虑,年纪还小。
隔膜的感觉像被孤身丢进深渊。她不明白为何自己的初恋会谈成现在这种模样。明明本该是青春美好的事,她却一天到晚担心这那,怕被人发现,怕意外怀孕,怕被他丢弃以后无处可去,怕人生彻底烂掉。
“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大钟揉着她的脑壳,“周末多做些喜欢的事吧,不想做的事情不用勉强。我看到你的插花了,很有花鸟画的韵味。第一眼就被治愈了。”
他说她勉强,应该看到了糟糕的作文,实在觉得惨不忍睹吧。太羞耻了,简直像光着屁股被揪住一样。
小钟急匆匆地给自己找台阶下,“我本来就不适合读书。”
然而,她合该接受这份无条件的溺爱,似金丝雀被豢养吗?
果然还是不甘心吧。
大钟弯腰抱她,但她将他推开,焦躁不安地跳起来。
“我不能一直这样摆烂下去。”
“为什么不继续做擅长的事?正好之前的画在网上很受欢迎,往这个方向努力看看呢?”大钟叫住她,冷静地分析利害。
“但这不代表我能画出能卖的作品。毕竟我是半路出家,还是学国画的,比不过那些画了十几二十年的科班大佬。网友肯定我,好像只是善意地鼓励一个爱画画的小姑娘,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你不也自己画了十多年吗?你的十年不是十年?”
“那不一样。”小钟急道。
大钟又退一步,“只是当成爱好,也不再画?”
“现在哪有这个心情。”她黯然垂头,“我觉得自己没有出路了。果然还是好好读书来得正经吧。”
“是什么人、什么事让你不敢再提笔了?”大钟相当锐利地明知故问。
憋屈已久的小钟当场炸毛,“你少自以为是。我不想画就是不想画,没有别的理由。”
其实很想画,只是找借口逃避的心情占了上风。吼出相反的话时小钟才意识到。
他耐着性子讨好媚笑,埋首吻她的指尖,黯淡的眼神却藏不住倦意,“为我再画一次吧。”
还是一样的话。既然劝过没用,又何必一说再说?如果作画的意义是为别人,那她更不想提笔了。往昔被辜负或背叛的种种还历历在目。约定了陪伴的人最后都离她而去,她还一个人傻乎乎等在原地。
小钟非但没领情,反而觉得他很烦,“别把我当傻子哄。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我不会为任何人画,别再说了。”
大钟也不客气,转身将她圈进角落,逼她直视自己的眼睛,“照你这么说,因为别人放弃自己想做的事,不是一样愚蠢?”
她蓄了一股劲大声道:“我没有——”
他提前察觉到小钟要吵架,用吻封了唇,不让她再说一句。
气恼变成崩溃,她拼命反抗,扯住他的手臂,两个人纠缠着滚落到地上。她忍着痛从他身上爬起,抬头看见耀眼的灯光,忽然感到自己反抗他也毫无意义,哇的一声大哭出来。
他会任由她欺负,但现实不会。
“不说这个了。”
大钟的不战而退并非谦让,更像是轻蔑于她,这反倒激发小钟恋战的心思。她当即抬手甩了他一巴掌。
这一下打得很重,自己的手也失去知觉麻痛许久,她不敢想象大钟的感受。
他的脑袋侧敲到地板,头发凌乱得飞散,发丝的反光处不细看就像白发,似比平日更柔软。
小钟非但没有怜惜,反而从中感受到无法无天、暴戾的快意。掌控的感觉像吸毒一样让人上瘾。
终于,终于她可以将身上背负的一切通通发泄出去。
“所以呢?”大钟仍望着别处,冷冷问,“我要怎么做你才满意?”
另一只手垂在他的心窝,剧烈的跳动炽热,恍若再进一寸,就能将他的心脏握进手中。她用力抓下去,他仍是不为所动的姿态。
大钟就是这点最让她讨厌。高高在上,不把人放在眼里,对什么事都淡淡的,漠不关心。无论怎样激他都像拳头打在棉花上,一会将她当成无知小孩哄骗,一会又希望她足够成熟,能冷静独立地决定很多大事。哪怕在相识的过程中,他给了她很多意外的心动,讨厌也一直没有改变。
没法和解的。
小钟龇牙咧嘴。
“如果是住在一起让你不自在,那就分开住。我给你在学校附近找房子,钱的事不用担心。我会时常来看你。”大钟道。
这一天比想象中更快来了。既然想好体面周全的方式,也就是真心想赶她走。小钟也恨阴晴不定的自己,可情绪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怎么都拴不住。
他的话很明白,分开未尝不是一种对彼此都好的选择。但她的自尊心难以接受。被她一手搞砸的事情已经太多。如果连和他同居都做不到,她好像就真的一无是处了。
“不要……不要赶我走。我会……我会控制自己的脾气。”
小钟慌慌张张将他松开,佝偻着腰啜泣,渐渐萎在地上。
哭了一会,他便从后将她圈住,娴熟地擦眼泪,似她自己身上多长了两只手,并沙哑着劝道:“我只是看你这些天太累了。算了,也放心不下你一个人。”
小钟为自己还被爱着感到庆幸又罪恶。毫无疑问,这是她恶劣的地方,好像每次都要闹到事情弄坏,才能够检验他的真心,像“狼来了”的游戏。
还能奏效几次呢?
不管了。至少现在,她可以释怀那些不着边际的远虑,痛痛快快哭一场。
“你也太能忍了,憋这么久才哭出来。”他拍着她的肩道。
止住哭泣许久,堵塞的鼻子才重新闻到他身上的幽香。雨过天晴的感觉很安宁。她望着天花板自嘲道,“我怎么总在你面前哭?”
“说明你还年轻,我是哭不动了。”
她听他的语声有些怪,反手搓他的脸,指尖却碰到似有若无的潮意。
“你哭了。”
他的呼吸声沉重,久无回应。
小钟没想到自己对他的影响竟会这么大,或许她坏掉的时候他也坏掉了。
“白痴。”她温柔又怜惜地骂,带着一点不想说话的嫌弃。
他侧头来咬她的唇,一回回都被躲开。她故意往他嘴边塞橘子嘲弄,却一不留神被捉住手腕,掀翻在地。
“干嘛?”大钟红着脸,眼眶湿润,又变成流泪猫猫的样子,想凶也凶不起来。
这模样教她怎么看怎么怪。
是不是有几分像自己?他以前应该不是这样。
小钟皱起眉又要恼。
他连忙拉回她的注意力,“是不是非要我说,乖乖做我的女人,你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