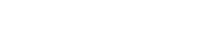郡主娘娘的身体愈发虚弱。
旁人说,上了年纪的人都是这样。
莫名发呆,忽地看不清眼前的东西,手脚发颤。
此外,她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
醒着也有些懵懂,记忆错乱。
有时,她把宝知认成谢皇后,嘱咐她在宫中要谨言慎行,莫要同陛下离心。
有时,将宝知认作乔霏,叫她放宽心,梁礼是好孩子,定会护住她的。
宝知又是当国母又是扮母亲,每次来侯府请安,回去时总显得憔悴一圈。
可她还是时不时递了帖子,无论是向乔氏请教婚嫁礼仪,抑或治家之理,总先去决明堂瞧上一瞧。
现下郡主娘娘又陷入沉睡,宝知在床沿边绣凳略坐了坐,伸手轻握郡主娘娘的手。
不复十年前她牵着宝知去见女师傅时的紧绷与细腻。
松垮的皮肉像是蟒皮,只勾连着筋骨。
可她的腕子却骨架分明,弯曲时豌豆骨高高耸起,硌得宝知掌心发痒。
屋内除却月支香的余味还有一丝熟悉又陌生的味道。
宝知往床头架子上一看,一把铜锡嵌蓝宝石长烟枪跃然入她眼,她心中悚然,明白这味道来源。
她大叁暑假曾出去上过四周的夏课,学院租的别墅所在的社区都是合作大学的学生。
因都是同专业的,出来交换的学生与周围本校学生经常接触。
有天隔壁那栋开派对,给她发消息,可巧她在帮堂妹整理竞赛资料,找个理由推了。
第二日一早,发现一起上学的朋友没有在房间,发消息也不回,她纠结了许久,直接上隔壁敲门,就见房子主人一脸懒倦地迎接。
那时,整栋房子弥漫着这股味道。
最后,她是在某个房间的浴室找到昏睡过去的朋友,怎么拍打都不醒,她急得要打叁位号码,被参加派对的其他同学联合阻止。
她后知后觉,他们在派对上公然吸食一些打擦边球的东西。
好在朋友没有碰,只是喝烈酒喝得太醉断片。
现在郡主娘娘也开始循序渐进地吸这些东西。
宝知没有惊动她,只将她的手放回被衾,垂着头由绿苏送出决明堂。
惠娘等人看出宝知的心境起伏,不敢打扰,只屏息凝神随着。
宝知似是踩在棉花上,一步一步都不由自己。
死亡。
这二字不难写,却难接受。
郡主娘娘离死亡不远了。
这个时代不同于她过去的时空,能活上50的,都是高寿。
在死亡面前,不管是王侯将相抑或平民百姓,都是一视同仁。
她怎么能衰败呢,她应该总是嬉笑怒骂,鲜活泼辣,肚子里有说不完的笑话与故事,抽屉里有收不完的香糖果子。
“姑娘!”惠娘疾步上前扶住她,她才发觉自己走得歪歪扭扭,都要丢入小池塘。
“没事,我不过是有些乏了。”
惠娘低低哎了一声。
可过了这条小道,宝知就逼着自己不能流露一丝内心的真意。
所有眼睛都盯着呢,她不能显出脆弱。
正是她择了条小道抒发心境,同那身着黑衣金丝衮底的男人隔着围墙错身而过。
宝知并未察觉,可那厢男人却停下脚步,问侍从:“似是一阵芍药花?”
周寄摇头:“臣并未嗅到。”
男人若有所思。
邵衍今日无事,却不想昨日回府收到谢四爷的传话。
故而一大早沐浴更衣,收拾得似是进宫面圣般。
他按惯例先要向府里老夫人请安,却听管事道郡主娘娘不得空。
邵衍心中一沉,面上不显,只温文一笑应诺。
但由小厮引路时心中不住胡思乱想。
可是那日书房僭越叫郡主娘娘或南安侯知晓,而不喜?
他无可辩驳。
一至庆风院,就见守门的婆子喜笑颜开:“大姑爷来了。”
邵衍顷刻红了耳垂。
自垂花门转入,就见院中央摆着张黄花梨长书案,两头摆着纸墨笔砚,还有两摞高高的红柬,案几两头各对放着把祥云雕花圈椅,边上还有几把玫瑰椅。
“啊,容启来了。”
“师兄!”
“姐夫!”
“衍大哥!”
谢四爷、乔氏同喻台还有源清曼叁兄妹都在。
邵衍忙上前行礼。
谢四爷今日告假就是为了候着这位准侄女婿,他本懒得上心,可那日他在静心堂表现深得谢四爷心,更不说宝知同他洽谈后整个人的轻快。
“今日都是自家人,不谈避嫌不避嫌的。”谢四爷道。
宜曼拍着手道:“咦,姐夫到了,姐姐还没来。”
“说曹操曹操到!”乔氏眼尖捉到院门那一闪的星郎裙落下的裙纱,刚调侃,就见宝知从垂花门外快步走入。
她瘦了一些,本就尖小的脸藏在发鬓里,衬得一双桃花眼黑白分明,樱唇轻抿,嗔怪:“哼!竟叫你拔得头筹!衬得我的迟到这般显眼。”
这一句黏黏糊糊的撒娇,若二人不熟定是叫邵衍诚惶诚恐许久,可交心后一听,那股甜意顺着脊柱攀爬,叫邵衍快要酥倒。
当着长辈面他不敢放肆,可一开口,就是不成句子的讷讷。
喻台见邵衍羞得快要掩面而逃,笑嘻嘻地和表哥表弟一道拥簇着邵衍在案几一头的圈椅坐下。
邵衍在谢四爷的示意下打开一看,内里空白,可他从印花就知用途。
宝知施施然在对面落座,举着笔对他道:“原先拖久了,今日才抽出一日大家都有闲暇来写请柬。”
这样热热闹闹一大家一道来讨论宴请情形,是邵衍第一次经历的。
以往长泰郡主宴客自有丫头婆子秉着册子请客,哪里要主人家来处理。
可这份亲近与温馨却是再精细的册子也无法比过的。
说是一起写,也就是宝知与邵衍二人动笔,弟弟妹妹在一边捣乱。
“这个张二公子以前同我斗过嘴,不要请他!”喻台说。
邵衍好脾气地应下,将写了一半的请柬丢到一边。
可松清道:“他弟弟张六跟我关系好,我们若是越过张二,请了张六,那张六就要吃编排了。”
邵衍又将那张写了一半的请柬捡回来,继续写。
松源道:“若是这样,何苦害得他们家里乱糟糟,不如都不请。”
“不行!他是我好友,我说了我大姐姐成亲请他来玩,怎能言而无信?”
……
谢四爷只不过是一打头跟他盘点一些京内姻亲与内里正守孝的人家,余下任由孩子们胡闹。
宝知这头在写女客,只有一个宜曼在玩闹,压力倒是小。
乔氏坐在一旁,时不时饮口茶,指导宝知哪些人必然要请,哪些人可有可无。
她悠然自得,抬头一看,见邵衍被几个弟弟拉扯着评理,鬓边都落下碎发,忍不住低头咬唇一笑。
宝知心中却想,若是邵衍做了父亲,也会是这样,是个温柔的好父亲。
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啊。
家庭的温暖抚慰了她对死亡与离世的恐惧。
庆风院里洋溢着春末夏初的向荣,只不过是几丈的距离,却将院外人隔绝在这片温馨之外。
今日还有些风,见桥伺候着邵闻璟多着了件外袍,可他仍然遍体生寒。
隐约可见的院中央风光美好得似一幅画,眉眼漂亮的男女相对而坐,长辈们带着慈爱任由孩子们打闹。
呵!多美!
敞开的院门却犹如无形的高墙。
墙这边是春,墙这头是冬。
他们是一类人。
他是一类人。孤家寡人。
外祖母内里已被病痛与忧虑掏空,整个人都衰败下去,只得用最好的药吊着。
他带着少有的茫然在侯府里漫无目的地走着。
邵闻璟向来心狠,对自己狠,对别人更狠。
不能怪他,他亲眼看着父亲被最信任的人所害。
他不狠,就轮到他下一个被端上桌吃干抹尽。
故而他忠实地信奉等价交换。
胜邪是捡来的野狗,需要有口饭吃,有块干燥的地面睡,邵闻璟给予他所需,才能更得心应手地使这把剑。
周寄是被赶于偏房底下生出的嫡出好竹,渴望振兴大房,为被逼死的父母正名,邵闻璟给他东宫这块匾牌,叫他堂堂正正地从正门接受叔叔婶婶的请罪。
东宫所有人的把柄与痛点事无巨细记录在他心底。
他不写手札。只有藏在心底的才是秘密。
可是郡主娘娘不同。
他曾经一味认为自己是她的秘密武器,她拖着大病痊愈的身子大张旗鼓站在东宫门口,将被烟火熏得满脸黢黑的他勉强抱在怀中,用肉身一路护送。
她为他谋策,为他请老师,为他造势,甚至从他刚出生时就布局,从遥远的成安埋下一粒种子,等到时机成熟,再将培养许久的花奉上,过关斩将,一路芬芳,最后亲手恭送他登上最高的位置。
等到现在,他才肯承认,她对他的爱远远压过对权势的审时度势。
他那满足自身需求总要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时再展开的性格已经将他误了一次——子欲养而亲不待。
时不我待啊。
邵闻璟由此及彼,从偏执追寻的那毫无突破口暗恋猛然惊醒,发觉自己真是大错特错了。
他是皇帝,还需自洽?他是天底下最尊贵的人,有的是人替他描补。
多年后,即便他身负骂名,也要同她一道纠缠。
不死不休。
胜邪就见主上脸上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表的笑意,似是洒脱,似是沉沦,随后就见邵闻璟往谢四爷所在院落投去深深一眼,他不知君主何意,只是无意瞥见其垂于身侧的右手无意识伸张再握紧,最后紧紧握住。
待到回宫,平云正纠结地候在殿口,一见今上仪仗,忙迎了上来:“陛下可算回来了。”
景光帝的心情显然不错,这叫平云松了口气,每每他从南安侯府归来总是叫人生寒,今日看来郡主娘娘有所好转,平云要说的话也好送出:“黛宁宫那位……”
他往上偷觑一眼,见景光帝并未流露不耐,反而兴致勃勃,放心大胆地复道:“婕妤娘娘道是抄写经文数月,已修身养性,太医号脉,约莫阴盛阳衰,故而龙子躁郁,所以想请……”
俊美的君王发出一声轻笑,平云即刻不语,似口中塞了茄子。
“阴盛阳衰,阴盛阳衰。”他听到主上轻声道:“婕妤幼年生于陇西,想来自然是思念家乡。”
邵闻璟站在高耸的阶梯上,承着落日洒下最后的温度,残留的斜阳似是把长刃,斜斜割过他的轮廓,仅一眼被黄河琉璃般的余光映照得熠熠生辉。
可余下的阴影逐渐攀升,将他吞噬。
在明暗交接时,他深深吸了口气。
落日终于落下,早已挂起的月亮力量微弱,只扭扭捏捏地洒下些许白光。
可太吝啬的施舍终究无法照亮紫宸殿的巍峨。
宫人们按照规矩点起蜡烛,重新照亮了黑暗中的男人。
可那光只能勉强点缀衮袍上的刺金,帝王仍然浸泡于黑暗。
好了,他沉默的时长已经足够。
“养了这么久的人,也该做些事了。”
———
旁人说,上了年纪的人都是这样。
莫名发呆,忽地看不清眼前的东西,手脚发颤。
此外,她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
醒着也有些懵懂,记忆错乱。
有时,她把宝知认成谢皇后,嘱咐她在宫中要谨言慎行,莫要同陛下离心。
有时,将宝知认作乔霏,叫她放宽心,梁礼是好孩子,定会护住她的。
宝知又是当国母又是扮母亲,每次来侯府请安,回去时总显得憔悴一圈。
可她还是时不时递了帖子,无论是向乔氏请教婚嫁礼仪,抑或治家之理,总先去决明堂瞧上一瞧。
现下郡主娘娘又陷入沉睡,宝知在床沿边绣凳略坐了坐,伸手轻握郡主娘娘的手。
不复十年前她牵着宝知去见女师傅时的紧绷与细腻。
松垮的皮肉像是蟒皮,只勾连着筋骨。
可她的腕子却骨架分明,弯曲时豌豆骨高高耸起,硌得宝知掌心发痒。
屋内除却月支香的余味还有一丝熟悉又陌生的味道。
宝知往床头架子上一看,一把铜锡嵌蓝宝石长烟枪跃然入她眼,她心中悚然,明白这味道来源。
她大叁暑假曾出去上过四周的夏课,学院租的别墅所在的社区都是合作大学的学生。
因都是同专业的,出来交换的学生与周围本校学生经常接触。
有天隔壁那栋开派对,给她发消息,可巧她在帮堂妹整理竞赛资料,找个理由推了。
第二日一早,发现一起上学的朋友没有在房间,发消息也不回,她纠结了许久,直接上隔壁敲门,就见房子主人一脸懒倦地迎接。
那时,整栋房子弥漫着这股味道。
最后,她是在某个房间的浴室找到昏睡过去的朋友,怎么拍打都不醒,她急得要打叁位号码,被参加派对的其他同学联合阻止。
她后知后觉,他们在派对上公然吸食一些打擦边球的东西。
好在朋友没有碰,只是喝烈酒喝得太醉断片。
现在郡主娘娘也开始循序渐进地吸这些东西。
宝知没有惊动她,只将她的手放回被衾,垂着头由绿苏送出决明堂。
惠娘等人看出宝知的心境起伏,不敢打扰,只屏息凝神随着。
宝知似是踩在棉花上,一步一步都不由自己。
死亡。
这二字不难写,却难接受。
郡主娘娘离死亡不远了。
这个时代不同于她过去的时空,能活上50的,都是高寿。
在死亡面前,不管是王侯将相抑或平民百姓,都是一视同仁。
她怎么能衰败呢,她应该总是嬉笑怒骂,鲜活泼辣,肚子里有说不完的笑话与故事,抽屉里有收不完的香糖果子。
“姑娘!”惠娘疾步上前扶住她,她才发觉自己走得歪歪扭扭,都要丢入小池塘。
“没事,我不过是有些乏了。”
惠娘低低哎了一声。
可过了这条小道,宝知就逼着自己不能流露一丝内心的真意。
所有眼睛都盯着呢,她不能显出脆弱。
正是她择了条小道抒发心境,同那身着黑衣金丝衮底的男人隔着围墙错身而过。
宝知并未察觉,可那厢男人却停下脚步,问侍从:“似是一阵芍药花?”
周寄摇头:“臣并未嗅到。”
男人若有所思。
邵衍今日无事,却不想昨日回府收到谢四爷的传话。
故而一大早沐浴更衣,收拾得似是进宫面圣般。
他按惯例先要向府里老夫人请安,却听管事道郡主娘娘不得空。
邵衍心中一沉,面上不显,只温文一笑应诺。
但由小厮引路时心中不住胡思乱想。
可是那日书房僭越叫郡主娘娘或南安侯知晓,而不喜?
他无可辩驳。
一至庆风院,就见守门的婆子喜笑颜开:“大姑爷来了。”
邵衍顷刻红了耳垂。
自垂花门转入,就见院中央摆着张黄花梨长书案,两头摆着纸墨笔砚,还有两摞高高的红柬,案几两头各对放着把祥云雕花圈椅,边上还有几把玫瑰椅。
“啊,容启来了。”
“师兄!”
“姐夫!”
“衍大哥!”
谢四爷、乔氏同喻台还有源清曼叁兄妹都在。
邵衍忙上前行礼。
谢四爷今日告假就是为了候着这位准侄女婿,他本懒得上心,可那日他在静心堂表现深得谢四爷心,更不说宝知同他洽谈后整个人的轻快。
“今日都是自家人,不谈避嫌不避嫌的。”谢四爷道。
宜曼拍着手道:“咦,姐夫到了,姐姐还没来。”
“说曹操曹操到!”乔氏眼尖捉到院门那一闪的星郎裙落下的裙纱,刚调侃,就见宝知从垂花门外快步走入。
她瘦了一些,本就尖小的脸藏在发鬓里,衬得一双桃花眼黑白分明,樱唇轻抿,嗔怪:“哼!竟叫你拔得头筹!衬得我的迟到这般显眼。”
这一句黏黏糊糊的撒娇,若二人不熟定是叫邵衍诚惶诚恐许久,可交心后一听,那股甜意顺着脊柱攀爬,叫邵衍快要酥倒。
当着长辈面他不敢放肆,可一开口,就是不成句子的讷讷。
喻台见邵衍羞得快要掩面而逃,笑嘻嘻地和表哥表弟一道拥簇着邵衍在案几一头的圈椅坐下。
邵衍在谢四爷的示意下打开一看,内里空白,可他从印花就知用途。
宝知施施然在对面落座,举着笔对他道:“原先拖久了,今日才抽出一日大家都有闲暇来写请柬。”
这样热热闹闹一大家一道来讨论宴请情形,是邵衍第一次经历的。
以往长泰郡主宴客自有丫头婆子秉着册子请客,哪里要主人家来处理。
可这份亲近与温馨却是再精细的册子也无法比过的。
说是一起写,也就是宝知与邵衍二人动笔,弟弟妹妹在一边捣乱。
“这个张二公子以前同我斗过嘴,不要请他!”喻台说。
邵衍好脾气地应下,将写了一半的请柬丢到一边。
可松清道:“他弟弟张六跟我关系好,我们若是越过张二,请了张六,那张六就要吃编排了。”
邵衍又将那张写了一半的请柬捡回来,继续写。
松源道:“若是这样,何苦害得他们家里乱糟糟,不如都不请。”
“不行!他是我好友,我说了我大姐姐成亲请他来玩,怎能言而无信?”
……
谢四爷只不过是一打头跟他盘点一些京内姻亲与内里正守孝的人家,余下任由孩子们胡闹。
宝知这头在写女客,只有一个宜曼在玩闹,压力倒是小。
乔氏坐在一旁,时不时饮口茶,指导宝知哪些人必然要请,哪些人可有可无。
她悠然自得,抬头一看,见邵衍被几个弟弟拉扯着评理,鬓边都落下碎发,忍不住低头咬唇一笑。
宝知心中却想,若是邵衍做了父亲,也会是这样,是个温柔的好父亲。
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啊。
家庭的温暖抚慰了她对死亡与离世的恐惧。
庆风院里洋溢着春末夏初的向荣,只不过是几丈的距离,却将院外人隔绝在这片温馨之外。
今日还有些风,见桥伺候着邵闻璟多着了件外袍,可他仍然遍体生寒。
隐约可见的院中央风光美好得似一幅画,眉眼漂亮的男女相对而坐,长辈们带着慈爱任由孩子们打闹。
呵!多美!
敞开的院门却犹如无形的高墙。
墙这边是春,墙这头是冬。
他们是一类人。
他是一类人。孤家寡人。
外祖母内里已被病痛与忧虑掏空,整个人都衰败下去,只得用最好的药吊着。
他带着少有的茫然在侯府里漫无目的地走着。
邵闻璟向来心狠,对自己狠,对别人更狠。
不能怪他,他亲眼看着父亲被最信任的人所害。
他不狠,就轮到他下一个被端上桌吃干抹尽。
故而他忠实地信奉等价交换。
胜邪是捡来的野狗,需要有口饭吃,有块干燥的地面睡,邵闻璟给予他所需,才能更得心应手地使这把剑。
周寄是被赶于偏房底下生出的嫡出好竹,渴望振兴大房,为被逼死的父母正名,邵闻璟给他东宫这块匾牌,叫他堂堂正正地从正门接受叔叔婶婶的请罪。
东宫所有人的把柄与痛点事无巨细记录在他心底。
他不写手札。只有藏在心底的才是秘密。
可是郡主娘娘不同。
他曾经一味认为自己是她的秘密武器,她拖着大病痊愈的身子大张旗鼓站在东宫门口,将被烟火熏得满脸黢黑的他勉强抱在怀中,用肉身一路护送。
她为他谋策,为他请老师,为他造势,甚至从他刚出生时就布局,从遥远的成安埋下一粒种子,等到时机成熟,再将培养许久的花奉上,过关斩将,一路芬芳,最后亲手恭送他登上最高的位置。
等到现在,他才肯承认,她对他的爱远远压过对权势的审时度势。
他那满足自身需求总要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时再展开的性格已经将他误了一次——子欲养而亲不待。
时不我待啊。
邵闻璟由此及彼,从偏执追寻的那毫无突破口暗恋猛然惊醒,发觉自己真是大错特错了。
他是皇帝,还需自洽?他是天底下最尊贵的人,有的是人替他描补。
多年后,即便他身负骂名,也要同她一道纠缠。
不死不休。
胜邪就见主上脸上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表的笑意,似是洒脱,似是沉沦,随后就见邵闻璟往谢四爷所在院落投去深深一眼,他不知君主何意,只是无意瞥见其垂于身侧的右手无意识伸张再握紧,最后紧紧握住。
待到回宫,平云正纠结地候在殿口,一见今上仪仗,忙迎了上来:“陛下可算回来了。”
景光帝的心情显然不错,这叫平云松了口气,每每他从南安侯府归来总是叫人生寒,今日看来郡主娘娘有所好转,平云要说的话也好送出:“黛宁宫那位……”
他往上偷觑一眼,见景光帝并未流露不耐,反而兴致勃勃,放心大胆地复道:“婕妤娘娘道是抄写经文数月,已修身养性,太医号脉,约莫阴盛阳衰,故而龙子躁郁,所以想请……”
俊美的君王发出一声轻笑,平云即刻不语,似口中塞了茄子。
“阴盛阳衰,阴盛阳衰。”他听到主上轻声道:“婕妤幼年生于陇西,想来自然是思念家乡。”
邵闻璟站在高耸的阶梯上,承着落日洒下最后的温度,残留的斜阳似是把长刃,斜斜割过他的轮廓,仅一眼被黄河琉璃般的余光映照得熠熠生辉。
可余下的阴影逐渐攀升,将他吞噬。
在明暗交接时,他深深吸了口气。
落日终于落下,早已挂起的月亮力量微弱,只扭扭捏捏地洒下些许白光。
可太吝啬的施舍终究无法照亮紫宸殿的巍峨。
宫人们按照规矩点起蜡烛,重新照亮了黑暗中的男人。
可那光只能勉强点缀衮袍上的刺金,帝王仍然浸泡于黑暗。
好了,他沉默的时长已经足够。
“养了这么久的人,也该做些事了。”
———